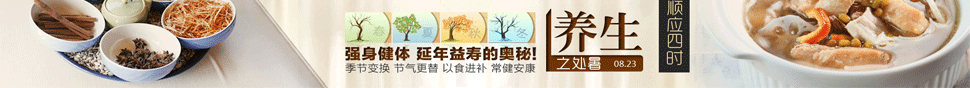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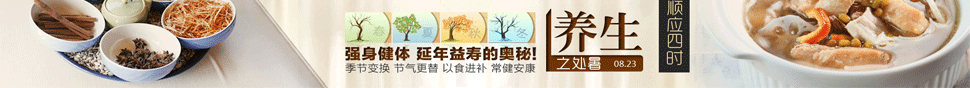
▲走,去吃腊味煲仔饭!(图片来自网络)
辛丑年冬月,一场好大的寒潮,夜里坐在灯下,听得北风一阵紧似一阵。岭外的冷意最宝贵,当下焚香煮茗,清淡的仪式感,总不教寒潮空来。忽地又想起一事,跟小熊说:“明天可以吃腊味煲仔饭咯!”
其实煲仔饭一年四季都能吃,但总觉得冷天吃最应景。想想看,冻得微微凝滞的空气里,一只犹在“滋滋”响的砂锅带着腾腾热气搁到面前桌案上,揭开盖,腊肠油润,饭粒晶莹,青菜碧绿,米香、油香混着锅底焦香扑鼻而来,是尘世中微小却结实的快乐。
“煲仔饭”“人头饭”“油炸鬼”,皆是令北方人初闻惶然而后又调侃不已的岭南饭食名,其实“油炸鬼”不过是油条,“人头饭”指聚餐时座中一人上一碗米饭,“煲仔饭”的“仔”自然也不指幼儿,而是“小东西”之引申意,煲仔即小砂锅。煲仔饭是将饭与菜在小砂锅中一锅煮熟:先在煲底刷薄薄一层猪油,米和水放入煲中,明火煮至七八分熟;加入配菜,于米饭表面铺放均匀,小火焖五分钟关火;继续焗一刻钟开盖,放入焯熟的油菜,浇上调味酱汁即成。
尽管煲中有荤有素,米饭依旧是煲仔饭的灵魂。袁枚《随园食单》云:“饭者,百味之本。饭之甘,在百味之上。”稻米、米饭于农耕民族而言,是刻入基因的依恋。因此朱楼画栋奇花佳木的大观园要有一处泥墙茅屋、十里稻花的稻香村,也因此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之后,岸上那样多风景人物,顺理成章唱出的仍是“风吹稻花香两岸”,不思量,自难忘。好的煲仔饭,第一要讲究用米。本地最适合做煲仔饭的米,是增城出产的丝苗米。
“北五常,南丝苗”,一日三餐的饭桌上,粳米软糯,籼米清爽,五常米和丝苗米分别是粳米和籼米中的翘楚。据说明代增城白水山上有栖云寺,寺中两位僧人将在各处云游时收集的稻种杂种,逐渐育成上好稻种,并分给山下村民种植,村民们呼为“寺庙米”,后演变为“丝苗米”。丝苗米纤长莹白,煮熟后粒粒分明,不粘不烂,干爽有嚼劲,正是适宜做煲仔饭的特质。
那袁枚又道,“知味者,遇好饭不必用菜”,自是夸张说法。米饭再香,只嚼白饭难免单调。广式煲仔饭配菜花样繁多,腊味、排骨、金菇牛肉、香菇滑鸡、笋干猪肉、梅菜肉饼,皆可与好米搭配。只是我独爱广式腊肠,每回说吃煲仔饭,都特指腊味煲仔饭。
▲腊味煲仔饭。(图片来自网络)
想来与粤地有缘。幼时一回吃饭,家里炒了一盘腊肠,切薄片,红亮诱人,说是亲戚送来的广式香肠。嗜甜的我入口便吃一惊,竟有如此好吃的腊肠!比之家乡又辣又咸的香肠让我欢喜得多,就着腊肠饱吃两大碗米饭,那口甘香从此留在记忆里。如今混成半个粤人,对腊肠的偏好始终未变。后来见到网上许多人扎堆义愤填膺地控诉广式腊肠,“又甜又咸,还混杂着浓烈酒味,怎么吃?”才深感人类口味差别之巨大。
看过灌广式腊肠的描述,选肥瘦相间的猪后臀尖肉切片,去掉筋皮,而十斤肉要加入一斤白糖和半斤浓香型曲酒腌制,如此比例,难怪让吃不惯的人批评太甜且酒味太重。在喜欢的人看来,却是口感细腻、味道层次丰富的美食。腊味的绝配在我看来是米饭,且是爽脆弹牙的籼米饭,因此广式腊肠与丝苗米一相逢,当真胜却人间无数。
寒潮第二日,与小熊去了常去的煲仔饭店。一人点一份腊味煲仔饭,这家店还有好汤水,瑶柱菜胆炖瘦肉,鸡骨草炖龙骨,西洋菜瘦肉炖陈肾,雪梨南北杏炖猪腱,青榄瘦肉炖白肺,任凭选择。不多时两锅热腾腾的饭送上,揭开盖再均匀淋上调味酱汁。煲仔饭煲制时不加任何调料,酱汁的味道因而举足轻重。各家店的酱汁皆是用生抽、老抽、鱼露、芝麻酱、沙姜粉、冰糖等按比例配成的独家秘方。
温暖醇厚的香气里,菜心与腊味好比碧鹦鹉对红蔷薇。腊味中不仅有腊肠,还有数片广式腊肉,走的亦是香甜甘鲜的路子。搅拌中晶亮米粒渐渐被腊味的油脂和酱汁浸润,熨平味蕾的渴望。而我的癖好,是必要留少许白饭不教油脂与酱汁染到。小时候吃面条,爸爸总在面条刚入汤碗时飞快捞几箸吃掉,说“这来不及沾汤味的还能嚼出小麦清香”,我亦要留几口天然稻米香。袁子才未说谎,好饭自有滋味,那几勺白饭缱绻缠绵地,在齿舌间细嚼半天才舍得吞下,我可算得上“知味者”?
才吃小半,小熊问:“要不要帮你挖饭焦?”若说米饭是煲仔饭的灵魂,饭焦便是灵魂之眼。本地电视台一档文化知识竞技类节目,有题问唐朝时的“御黄王母饭”是今时哪种广东美食,参赛者异口同声抢答:煲仔饭!“御黄王母饭”见于唐代韦巨源的《烧尾食单》。烧尾宴曾在唐代长安盛行一时,是士人新官上任或官员升迁时招待同僚亲友的欢庆宴会。韦巨源拜尚书令时设烧尾宴答谢唐中宗,包括“光明虾炙”“葱醋鸡”“单笼金乳酥”等数十道菜的豪华菜单流传至今。按食单所载,“御黄王母饭”大约是以肉菜浇于黄米饭上。一个说法是御黄王母饭又由周八珍中的“淳熬”与“淳母”演变而来。周八珍为周朝宫廷宴上八道美食,后人注释云,“淳熬”是将煎肉酱与油膏加于白米饭上,“淳母”则是以同样配料加于黄米饭上。若说煲仔饭便是曾经的御黄王母饭,我有些不服,毕竟史料中看不出淳熬淳母和御黄王母饭是用小锅将饭菜一齐烹熟,这几种饭食听起来倒更像如今的盖浇饭,即粤人所谓碟头饭。而盖浇饭与煲仔饭的最大分别,是煲仔饭有诱人的饭焦呀!
▲金黄的饭焦。(图片来自网络)
用勺子沿锅底轻轻铲动,大块金黄饭焦被起出,嚼在嘴里酥香生脆,肉香米香焦香随咀嚼一层层沁出,似春来繁花次第盛开。小时候老家尚有柴火饭,蒸汽袅袅里饭香满屋,我跟妹妹每回都吵着要饭焦,外婆铲下饭焦,给我们一人分一小碗,再浇几勺辣椒炒肉的汤汁在上面,焦酥中混着肉汁的香辣,十分美味。如今回想起来只剩温柔的怅惘。煲仔饭的饭焦似乎比幼时吃到的更厚更脆,嚼完饭焦,再喝一碗五指毛桃炖龙骨汤,唇齿间一星燥气渐渐被中药香抚平,像阳光晒热的沙滩到夜里为月色笼罩,惟余宁静。玻璃门外,路人裹紧外套匆匆而行,众生皆苦,可如此简单的饭食仍能带来丰盛的快乐,这烟火人间毕竟值得我走这一遭。
▲这烟火人间毕竟值得我走这一遭。(图片来自网络)
《岭南花木镜》,彭焰著,南方日报出版社年8月出版,年6月第二次印刷
京东商城、卓越网、当当网及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有售
彭焰:作家,词人。现居广州。著有散文集《岭南花木镜》,词作收入《当代海内外诗词选》。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jigucaoa.com/jgcgj/11383.html